看完電影回家,不用上班的假日,在房間裡睡的天昏地暗。
林宥嘉唱:散步紐約街頭 快要吻的時候 閃耀你唇上的溫柔 怎麼忽然變成 電鑽鑽頭 一樓四樓七樓 Stereo大合奏 成年以來一直睡不夠 幹嘛休假樓上總有人 裝修......一覺睡到自然醒 不管這個胡鬧世代有多壞......
這是現下生活寫照。
炎熱的陽光穿透紗窗將你晒醒,你攤在床上貪戀著床鋪不願起身。翻來覆去幾次,伸手抄起右手邊的手機,就無線網路開始FB。
你回了幾則訊息,按了幾個讚也不清楚,友人一早看展打卡在中正紀念堂。假日那絕對人山人海,人聲鼎沸,最受不了吵鬧的你光想像那畫面就覺得胃經攣(其實是餓了?)。
Whatapp朋友問下午是否赴約?發楞了幾秒,佯稱大病初癒不宜外出宜在家養身。這理由說不上瞎卻彷彿農民曆上的宜忌,X月X日,宜發懶,忌會友。
旺盛的對流使得午後陰了天,傾盆大雨罩住這世界,原想出去吃遲了的早午餐,這下也甭出門。
眼光瞥見角落一隅的髒衣籃,你想起新版還珠格格爾康騎馬影片。youtube上他說他滿了,紫薇說她漫出來了,你望著髒衣籃,心想:這才是真的又滿又漫了出來。
自個兒的衣服還是自個兒洗,不過思及那台洗衣與脫水分開的「新穎全手動」機器就嘆氣。這樓3房2廳2陽台兼格局方正是吸引你們租下的原因,美中不足就一間浴室跟這台全手動引水、停水、排水、脫水的舊型洗衣機。
每回洗衣就得耗上許多時間,擔心沒洗乾淨得重複三次引水、停水、排水的動作,在加上一次脫水。那過程裡,你不免問自己:何以離家生活?
在家裡宛如大少爺,吃喝拉撒睡都有人侍奉,茶來伸手飯來張口,衣服髒了有人洗,電費水費瓦斯費網路費通通有人繳,到底是為了什麼流浪呢?
理由是否正如張瑋栩寫:『我寫作並沒有向任何人交代己身言行舉止的意圖。我只是天真的以為,只要是從自己的房間出發,就一定可以找到世界的盡頭,而世界的盡頭應該就是可以讓我安身立命之處。』
你在找,安身立命之處嗎?
他總對你說:不自由毋寧死。你總疑惑,這樣的房間,或說,這樣的生活,是你要的嗎?
跟其他兩個非血緣關係人同個屋簷下,是便宜了誰?
吉田修一在著作《同棲生活》裡,描寫五位個性迥異截然不同的同居人,以一種「看似體貼卻又放任彼此的」共同生活,作為貫穿全書的核心主軸。
你從一個人獨居的套房搬進了這個共居的公寓,無非也企求一種隱形的照料。既能獨自生活又能在脆弱的時後,除了窩在房間裡,還能選擇跟室友喝啤酒打屁抱怨吐苦水,暫時忘記工作上的不順心或者曖昧對象死會帶來的打擊。
在房間以外,只是想要別人四兩撥千斤不那麼沈重嚴肅的建議與同仇敵愾,就能夠再面對醒來的明天。
在房間裡面,你是世界的王。
你曾經寫下:「一個空間,應該說,一個房間,不僅僅只是房間,是情感的依附,是世界的盡頭,是安身立命的地方,就不合該是個只用來睡覺、作愛的空間。
我如是想。
那些環繞在我身旁桌上的書籍、雜誌、手帳、信件、卡片、剪貼簿,都是我記憶的堆砌。衣櫥裡的包包、衣服、褲子,是我上班的武裝。我聽的音樂、我看的電影,我拍的照片,散落我的房間。
我的房間是我自己的化身。」
倘若我的房間是我自己的化身,那麼我就是孤獨的國王。
年紀越大,更懂得電影《非關男孩》,他寫「每個人都是一座孤島,我絕對相信這點,但其實有些人是群島的一部分,海底下其實緊緊相連。」
你想起搬進來的某天,三個人約好了開伙。你們準備了從深坑買回來的鴨血臭豆腐,家樂福買的金針菇與青菜肉丸子跟著下鍋;巷口買的白飯,夜市買的滷味上桌。清出原本擱滿雜物的餐桌,瓦斯爐上架,三個人坐下來,只不過是好好吃一頓晚餐。
「我知道,新的生活已經就緒,就等我加入,運用時間與精神和各種事物對話,並且再一次發現自己。
其實,天空怎麼會太高呢?我們都該有理由相信你摸到的,就是天空。」
終於,雨停了,洗好也晾好衣服,你盤算拎著書出門,往咖啡館前進。你想起他說:「那是我最遠的流放,而他們都還不知道。」
你說:「台北不會是你最遠的流放,而他們卻都這麼以為。」你對自己笑了笑,果然是難以取悅社的社員,還是一個人泡咖啡館比較實在。
出門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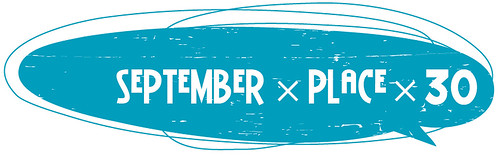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